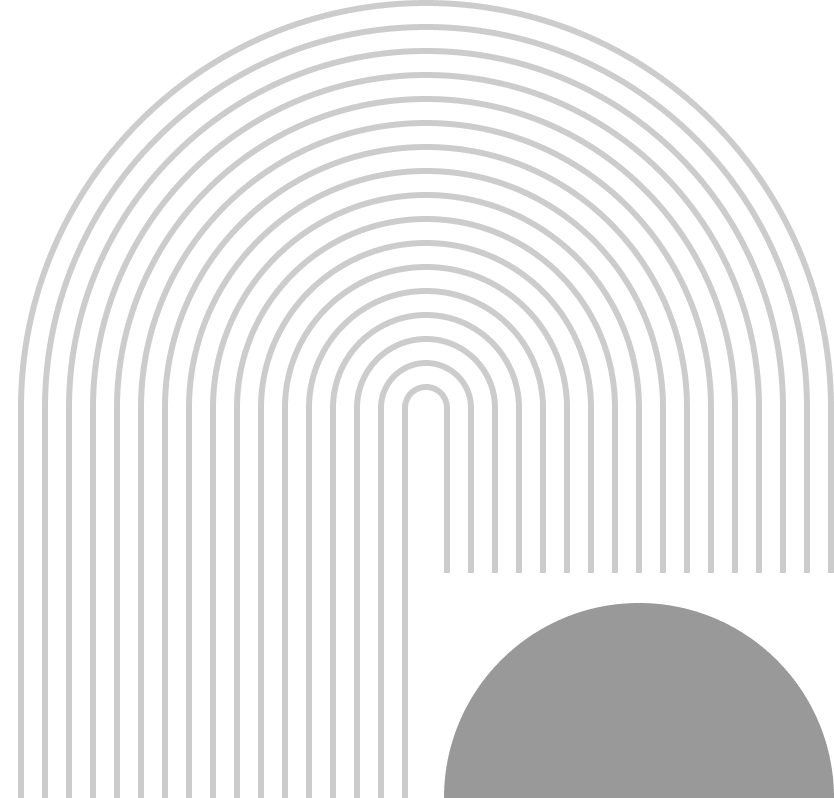(图源:《澎湃新闻》)
2.封闭式的提问
示例:高明喜欢日本的环境,用封闭式提问具体化:“是不是空气比较湿润?”“是不是街边亮着很多灯?”不一定得到确定回答,但鼓励受访者回忆、回想感受到的东西。
原文内容:
高明喜欢日本,她跟着律师去了三次。那里的空气澄净、湿润,夜晚,街边一排排商店闪着霓虹灯,商场里卖什么的都有。
而在家,日头总是不落,穿凉拖出门,回来时脚底就有一层沙子。她的行走范围只有以家为圆心的一小块,因为免疫系统损伤,她走到几百米外的道边都要大口喘气,有时走也走不回来。
从日本回到家一个人呆着,她又感到说不清的难受:那么好的一个地方,为什么曾经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?
四、外围采访的意义
1.丰富人物细节
示例:徐志夫对回忆对日本的感情有困难,于是与他的儿子聊。
中毒头几年,电视里,播着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,原本在病床上虚弱躺着的徐志夫一跃坐起,直着脖子,大喊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还我健康身体!”
2. 现在的状态和以前的状态不同,也许受访者本人不能明晰、直接地讲述以前内心的想法
原文内容:
那时候,李臣的身体逐渐变弱。日本律师告诉他,李臣要没了,证人就没了。
罗立娟回忆,吴凤琴曾说,李臣开始好好吃饭,之前有的药不愿吃,后来整箱整箱买。只要碰到上日本请愿、开交流会,李臣几乎从不拒绝,见到罗立娟会唠,“我要好好活着,我这还有任务没完成。”
……
多少年倏忽而过,罗立娟明显感觉,受害者都老了,他们的步子变慢了,头上也冒出了白发。几个年幼的孩子如今已长成了青年,当年的青年有些也有了孙儿。
李臣没法再想着那些创伤了。
3.外围采访对象对人物的观察与体会,为主题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与深度
为何会有表达能力的欠缺?
原文内容:
黑龙江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立娟回忆起第一次听“八四”受害者讲述中毒后的遭遇,他们急切地说,“水泡最开始是小红疙瘩,然后变成小绿豆粒儿那么大,又变成黄豆粒儿,然后鸽子蛋那么大,鸡蛋那么大,最大像馒头那么大。”
在她看来,那是找不到语言形容的迷茫。受害者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,只能用最贴近生活的食物来表述。侵华战争、化学武器,很少有人提及这些庞大的字眼。
不只是受害者,大多数人都对毒气弹和芥子气的性质无从得知。
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,底层人们如何去理解、表达自己的诉求。律师对受害者变化的留意:从关注自身权益到关注自身以外的更公共的话题,如化学武器的销毁。
原文内容:
多年漫长的诉讼过程,她也感觉到受害者的变化。
“历史是活的,不会死的。”
“我当初来的时候,我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赔我钱,但是现在,我个人也可以代表“八四”受害者——如果日本政府能尽快在中国销毁化学武器,我宁可放弃我的赔偿。”
受害者冒出来的三言两语,让罗立娟震惊和感动。最初,她感觉他们不太了解历史、政治,很多人是打工者,也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。提到中毒,他们会说“很痛苦,伤害挺大”。
慢慢,有时在法庭,有时在媒体见面会,或是民间团体接待、给外务省递材料的时候,受害者会临时触景生情,激动地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点,甚至放弃个体的权利。
五、人物报道情绪的把控与主题复杂性
1.悲情化 VS. 人物的尊严
相比对受害者报道的悲情化,呈现他们自我的应对和变化更重要,正是在痛苦之中的一些细节能让读者理解主题。
在医院病房采访李臣,刚开始接触会觉得他是需要帮助与关怀的老人,内心是伤口很深的人。但看到他病床旁边的鱼缸养鱼,不同意帮忙换水,体会到李臣的尊严,体会到他活下去的愿望。
原文内容:
吴凤琴不懂,为什么“不能让想爱的人去爱,想相爱却不能相爱”。
李臣记得,结婚时,家里拮据,他们就去动物园溜达了一小时。天空下着小雨,他俩打着伞,靠在一块。回到租的房子里,邻居帮他们打开门,说一声:“小两口,进屋吧!”一转眼,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2.以轻的东西写重的感情
原文内容:
徐志夫是一审的受害者代表。他整了一套西服,理了头发,什么也没拿,就带了一个皮兜过去了。
他不知道买什么,就在家附近买了20多个小小的福字,几块手绢儿,印着花的,叠好装到兜里。见到日本友好人士,一人给一个。
VS. 采访徐的儿子得到的另一细节:徐一下飞机打电话给儿子激动地说,我来日本了,代表病友为受害的人送去曙光。
文章选择了前一个更加贴近人物日常状态的细节。
原文内容:
“你没死呢!”“没呢!”“那谁呢!”“没了!”
每年体检,受害者们相聚在一起,诉说着只有彼此能理解的密语。
VS. 徐表达过“活一天算一天”的想法。但文章没有用这句绝望的话。
3. 报道主题的深化:人物如何超越自身
以往报道主题清晰,落入民族主义的叙事中。做这个选题一开始的可能预设是受访者们对日本国家、甚至人的愤怒。实际上发现并非如此。日本友好人士与律师团体对受访者的帮助,与日本民众有深入交流,是受访者本人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。于是还原与日本友人沟通的细节,勾画出主题的复杂性,展现受访者重新建立信念的方式与复杂的心态。
示例:受访者去到日本,见到繁华的大都市、有礼貌有秩序的民众,诉讼一直拖到和平年代,受访者们已经感受不到过去战争与现在的关系,但他们自己又是战争的受害者。
例如,高明对日本的印象与新鲜感,与日常焦虑无聊生活的对比;徐志夫碰到的90岁日本老太太,战争时在中国做过俘虏,也在东北医院做过大夫,用东北话聊天,徐觉得很亲切。